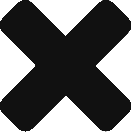-
Recent Posts
Recent Comments
- wangxiaoxin on 从一个华盛顿到另一个华盛顿
- 匿名 on 从一个华盛顿到另一个华盛顿
- 天天 on 异乡风味与中国胃
- GM on 我为什么要回国
- waking on 《虔诚的鳏夫》:什么时候中国导演也能这么自信就好了
Categories
Archives
- April 2020 (3)
- January 2020 (6)
- December 2019 (4)
- November 2019 (1)
- October 2019 (31)
- April 2018 (3)
- March 2018 (4)
- January 2018 (2)
- December 2017 (3)
- November 2017 (1)
- October 2017 (6)
- May 2017 (1)
- April 2017 (1)
- March 2017 (15)
- July 2016 (2)
- May 2016 (2)
- February 2016 (4)
- December 2015 (1)
- November 2015 (3)
- October 2015 (6)
- September 2015 (3)
- August 2015 (1)
- July 2015 (1)
- June 2015 (5)
- May 2015 (1)
- April 2015 (1)
- March 2015 (10)
- February 2015 (1)
- January 2015 (6)
- December 2014 (2)
- November 2014 (4)
- October 2014 (3)
- September 2014 (3)
- August 2014 (4)
- July 2014 (2)
- June 2014 (1)
- April 2014 (2)
- March 2014 (3)
- February 2014 (4)
- January 2014 (1)
- December 2013 (3)
- November 2013 (9)
- October 2013 (2)
- September 2013 (2)
- August 2013 (5)
- June 2013 (1)
- May 2013 (3)
- April 2013 (2)
- March 2013 (2)
- February 2013 (1)
- January 2013 (1)
- December 2012 (5)
- November 2012 (3)
- October 2012 (6)
- September 2012 (9)
- August 2012 (4)
- July 2012 (10)
- June 2012 (11)
- May 2012 (4)
- April 2012 (5)
- February 2012 (4)
- January 2012 (6)
- November 2011 (5)
- October 2011 (4)
- September 2011 (1)
- August 2011 (4)
- July 2011 (3)
- June 2011 (4)
- May 2011 (1)
- April 2011 (6)
- March 2011 (11)
- February 2011 (4)
- January 2011 (12)
- December 2010 (9)
- November 2010 (11)
- October 2010 (6)
- September 2010 (4)
- August 2010 (9)
- July 2010 (9)
- June 2010 (6)
- May 2010 (15)
- April 2010 (10)
- March 2010 (11)
- February 2010 (13)
- January 2010 (15)
- December 2009 (19)
- November 2009 (17)
- October 2009 (20)
- September 2009 (17)
- August 2009 (20)
- July 2009 (9)
- June 2009 (6)
- May 2009 (12)
- April 2009 (14)
- March 2009 (7)
- February 2009 (8)
- January 2009 (10)
- December 2008 (9)
- November 2008 (15)
- October 2008 (18)
- September 2008 (11)
- August 2008 (10)
- July 2008 (6)
- June 2008 (14)
- May 2008 (5)
- April 2008 (11)
- March 2008 (7)
- February 2008 (10)
- January 2008 (8)
- December 2007 (10)
- November 2007 (7)
- October 2007 (11)
- September 2007 (9)
- August 2007 (3)
- July 2007 (10)
- June 2007 (2)
- May 2007 (5)
- April 2007 (8)
- March 2007 (8)
- February 2007 (4)
- January 2007 (4)
- December 2006 (7)
- November 2006 (6)
- October 2006 (9)
- September 2006 (10)
- August 2006 (11)
- July 2006 (9)
- June 2006 (12)
- May 2006 (7)
- April 2006 (22)
- March 2006 (8)
- February 2006 (11)
- January 2006 (9)
- December 2005 (10)
- November 2005 (13)
- October 2005 (8)
- September 2005 (8)
- August 2005 (10)
- July 2005 (16)
- June 2005 (5)
- May 2005 (14)
- April 2005 (2)
Tag Archives: 王小心
《布达佩斯大饭店》:向逝去的世界致敬
《布达佩斯大饭店》的预告片就是渣。我开始看预告片的时候,还以为电影是一个拼盘杂烩的搞笑喜剧,看简介也是一样。结果发现电影原来是有情节的,于是当成一部侦探剧看了下去;结果发现情节上面是有主题的,于是当成文艺片接着看下去;最后发现不但有文艺,还有政治,还有历史,还有文化,端的是一部有境界、有层次,满足信达雅的电影。然后看到最后五分钟,直接在影院哭成泪人。 为什么呢?就好像一个小情小爱小清新的故事,开头你以为格局很小,就是主人公被卷入一场遗产纷争,有点悬疑,有点喜剧,有点黑色幽默;然后你发现两个主人公之间有超越国家、文化和价值观的友情,而看起来不起眼的小主人公还有自己的爱情,就觉得很温馨;然后发现在这个小情小爱的故事背后,政治和战争的阴云始终笼罩其上,一点一点吞噬掉人类的的文明和人情;最后有了一个高潮和喜剧结尾,你以为像《七十二房客》那样,皆大欢喜,各回各家各找各妈了,结果Jude Law多问了一句“最后呢?”发现你以为永远的幸福原来是如此短暂,小团圆的结局根本抵不过大时代的悲剧。根据茨威格的观点,这是一个时代的灭亡,人类最后的文明的消失(不知道他如果活到今天会怎么想),那些衣香鬓影的贵族没落了;那些人类文明的艺术品失传了;那个能为一个小小门童的命运奋起抗争的绅士被杀了;那个消失的世界早在古斯塔夫先生们意识到的很早以前就消失了;所以茨威格会自杀,就像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齐,更像明朝灭亡之后,那些辞官隐居、穷困潦倒的文人们,写下《陶庵梦忆》,做着怀念故国的梦。只有他,还孤独地活在这座曾经名贵云集、高朋满座的布达佩斯饭店中,住在电梯不到的楼顶仆人的房间中,不过是为了怀念亡妻那短暂且幸福的时光。 导演韦斯·安德森的风格实在太显眼了,在《月升王国》中就领教过,这部电影很多细节看起来都分外眼熟,比如律师断指的情节和《月升王国》里小女孩把耳钉往耳朵里刺流血的情节,分明是同一个人的黑色幽默加恶趣味。镜头的转换、场景设计的营造、漫画一样的色彩就更不用提了。
我为什么要回国
我原打算近期回国一游。很多朋友都觉得麻烦,时差、孩子、污染、请假。为什么要回国啊?他们说。 刚来美国时,觉得美国是旅途,中国是故乡,美国是生命中的多一份体验,领略大好河山、优秀制度、教育系统、工作体验。然后嘛……其实我没有想过然后。我竟然没有想过然后!潜意识里,我是觉得总有一个可以回去的地方,那里有我可以随便聊天的邻居、出租车司机,楼下可以下班回来去买的小米粥和烧饼,家里有可以窝在沙发里一看一晚上的北京卫视。 来美国之前,我在北京已经生活得很好。这个好不光是经济上的,更是人际上的、精神上的。我住在一套可以看西山的小房子里,挣着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工资,有很多朋友、熟人,下班后不愁没有娱乐的地方。看戏、看电影,三里屯和南锣鼓巷的小餐馆,国家大剧院我是常客,朋友甚至能给我弄来不要钱的前座票——这一切,除了前两点,我在美国都不可能实现。 在美国,我重新读了书,找到了工作,挣得比以前多,也买了自己的房子。然而,在这里永远不可能随便地找到朋友,路边没有随时能找到的来家里装窗帘的小工,保姆贵得要死,理发还要给小费,给电话公司打电话之前要先打好腹稿,文艺一点的话剧和各种奇特的电视台全都看不懂,工作中我做得比大多数人好,可是升职遥遥无期,他们还是更愿意提拔白人老板——我太理解了, 就像我在国内不想雇一个印度人一样。 所以,在美国,永远不可能生活得像在中国一样随意。 但是在美国五年之后,我发现中国也渐渐远离了我心中的故乡角色。 我在中国做媒介时,了解每一本杂志,认识90%的网站的销售;我的名片夹有十几本,每天开会,都可以了解到中国社会和消费者的最新发展趋势。可是现在,我不知道什么是滴滴打车,不知道余额宝,忘记如何使用银联的信用卡还要跟手机绑定,永远估计不好打车的时间和打到车的概率。上次阿里巴巴的CTO来西雅图讲座,我没有听过他说过的大多数游戏、八卦和产品。而且我发现,大部分听众都和我一样 ,对日新月异的中国社会充满了无知。 日新月异,真的是日新月异。你离开这个地方一年、两年,可能还没有什么感觉,因为你毕竟走在时代的前端;可是三年、五年过后,你觉得中国陌生。邻居搬走了,同事跳槽了,朋友升迁了,忙着做生意买房子,你连他们的孩子都没见过。你曾经最爱看的杂志倒闭了,最喜欢的理发师换了联系方式,你再也找不到他。更严重的是,我已经不能适应北京的天气、公交车上的抢座、饮食的辛辣和肮脏,与狭小的公寓。 然后中国变成了一个陌生之地。而美国,是熟悉却难以亲近的。 于是你变成了一个没有故乡的人。真真正正的没有故乡。没有任何地方是栖息之地。没有任何地方你可以用熟悉的交际方式认识新朋友,没有任何地方你可以说是真正了解,没有任何地方可以称之为家。 乔治·克鲁尼演过一部电影,叫《悬而未决》。他演一个繁忙的白领,空中飞人,像无足鸟一样脚不沾地。当我突然意识到这一点后,我发现我也像他一样,如浮空中,失去了立足的根本。 所以我回国,像是要抓住最后一根稻草,或空中的人需要一个支撑。当然这是毫无用处的——不管我选择在哪个地方居留下来,我都会离另一个地方越来越远。
Captain Phillips《菲利普船长》:啊,船长,我的船长
我一直对航海生活有向往心理。小时候听《军港之夜》,《大海啊故乡》,再大一点看《潮起潮落》,玩光荣的大航海4,水手说“我从小的愿望就是在甲板上仰望星空”,啊,多么浪漫。 我知道许多人和我有相同心理,然而真正的航海生活却远不如想象中浪漫。在茫茫的世界上飘荡,脚下没有坚实的土地,一眼望不到尽头的海水,没有淡水,没有伙伴,有的只是狭小的船舱、难喝的咖啡,内讧的船务人员,和不知什么时候会蹦出来的海盗。 Tom Hanks演得太真实。船长的苦闷、面对敌人的镇静、沉着有力的指挥、自我牺牲精神,甚至短暂的慌乱,都是一个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我不禁看到了他英雄的一面,也看到了他常人的一面,甚至看到了他被软弱的一面。被获救后他哭着对医护人员说:“谢谢,谢谢……”重复了一分钟,让在场观众无不为之动容。我想,一个真实的人,在生与死、血与火的枪口下被解救出来,能做到的最好,也无非如此了。我流泪甚至不完全是为了船长,也为了他的演技。 如果说Tom Hanks能得个奥斯卡最佳男主角,那演索马里海盗头子的那位起码可以得个最佳男配提名。他的演技有一度甚至让我以为他们是找到了真海盗来演。电影最令人击节的地方在于导演没有把他们完全当成反派,在镜头里,他们也是有想法有立场的、活生生的人。他们作海盗是迫于生计,索马里贫瘠的土地养活不了他们;他们驾驶着一艘破船,竟然可以占领几万倍之于他们的国际货轮,这种孤胆英雄的勇气和技术是被生活逼迫出来的,我们可以想象这些亡命之徒背后的心酸。他们贪婪、他们无知,以为一千万美圆只是美国人的随手小菜,但他们也有人性,甚至有着非洲人民与生俱来的那一点淳朴。“我们想要回家。”当他们发现事态已经无非控制时,这是他们最后的希望。 是与非并非事物唯二的两面,这是我看完电影最初的感受。这是一个英雄和一个有力的政府战胜敌人的故事,但故事里有无奈、有迂回,也有退缩;这也是一个破碎的家园、破碎的民族的故事,我无法赞同他们,但对他们的命运有了更多的思考。这是部成功的电影,也是部感人的电影。 http://www.wangxiaoxin.net
总把新桃换旧符
安是个七十多岁的美国老太太,在风景秀丽的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做志愿者。我和她同事的时候,有一天聊起传统文化。她问我,中国为什么要破四旧呢?破四旧有什么好处?我想了想,竟不知如何回答。最后我只能说,根据我的想象,几十年前,我们的长辈应该认为既然一切都是新的,那么旧的一切就都应该毁灭吧。其实我对自己的这个答案也非常不满意,因为我不知道旧的东西哪里惹着他们了——似乎没有一个国家,能把旧的东西毁灭得那么彻底。 然后安说,她曾经认识一个台湾女孩,对她自豪地说台湾在保护传统文化,比如繁体字方面比中国大陆做得好得多。她转过来对我说:“王小心啊,这是女孩子的原话,我也不知道保护繁体字是件好事还是坏事。”这一句“好事还是坏事”让我发现,美国人民对过去还真是不怎么看重。这很可能因为他们确实没什么历史——这点往往被中国人嘲笑的出发点,但更有可能是他们的历史确实不怎么光荣。美国人没有家谱也没有清明节,安跟我说,这是因为他们的祖先从旧大陆来的时候往往身无长物白手起家,他们压根就不希望记住过去的历史。是啊,谁会在衣食无忧的时候想到漂流海外呢? 【图片】安老太太家的感恩节火鸡 这提醒了我,其实中国人对“新旧”的敏感,强过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我们曾经用最残暴的方式毁灭那些祖先给我们留下的遗产,然而沧海桑田,破四旧的那些人们也许想不到有一天,被他们砸烂的佛像、文物,会登上一流的拍卖会,在国际富豪和豪门望族中风生水起。如今的中国沉浸在一种为古老文化、建筑、文物的丢失和毁灭而伤感的气氛中,随之而来的是对祖宗的文化的怀念,和对古旧事物的崇拜;曾经无人问津的古玩市场如今比股市还火,马未都上一趟央视就吸引了亿万粉丝,上至官员下至小学生纷纷开始学习“国学”。 我们似乎总在新旧的两极之间摇摆:我们可以谴责在埃及古庙上写下“到此一游”的孩子,但我们仍然毫不留情地拆去那些成为开发商障碍的城楼、牌坊、昔日的建筑。而那个问“新好还是旧好”的安,她家里的黄铜茶壶和樱桃木家具是意大利丈夫从欧洲海运过来的,几十年历史;家里占据一面墙的波斯挂毯,据说是祖父的父亲从土耳其购得。 的确,美国是一个只有几百年历史的国家,可是这几百年的历史也如同美国的喜怒哀乐一样,明明白白写在他们的脸上。他们从不过分崇拜历史,但历史已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这个年轻的国家给我们留下了一百多前年建造的国家公园,两百多年的大学,和更加古老的宪法。他们的历史“至今沿用”,他们的历史没有断层。 在学校读书的时候,有一次去参加校史讲座。档案馆长告诉我们,当年我们大学刚刚建立的时候,为了招生,校长主任在芝加哥挨家挨户去推广学校,情况估计比《中国合伙人》里面乐观不了多少。校长卖的是一张“永不过期的入学证”,意思是只要你付了学费让你儿子上大学(那时还没有女生),这张凭据可以在家族中世代流传,儿子的儿子,儿子的儿子的儿子……都可以免费上学。付一次学费造福万代,子子孙孙无穷匮也。 然后档案馆长说:“直到如今,每隔几年,我们还会看到拿着这张入学证的学生,被我们免费录取。”这所私校的院墙之外,当年的围墙还铸刻着建立的年份,创始人种下的大树枝繁叶茂,学校排名已直逼全美前十。 这就是美国人的历史。
丹佛记
作为美国中西部最大的城市之一,丹佛这个城市给我的印象与整个中西部给我的感觉一样:幅员辽阔,寸草不生,千篇一律的town center、商业区和公路。自芝加哥往西,开了几千公里见到的基本就是这幅德行,与东西海岸的风情万种大相径庭。可是人算不如天算,公司的技术中心就在丹佛,所以我与同事只能义无反顾地踏上东行之路。 丹佛的天气有两种:晴天或者下雪。由于极端远离海岸,又背临北美最大的落基山脉,丹佛的天气如同弹簧一样,不断在极冷和极热之间蹦跶,而且基本实现无缝链接。我们去的时候已经是四月下旬,西雅图的樱花都快要凋谢了;可是丹佛在我们去的第二天开始大雪纷飞。前一天还是春光明媚的十来度,第二天早上,我和同事只能百无聊赖地坐在车里,打火,暖车,等着车外一英寸厚的冰一点一点地融化,这个过程用去我们半小时,而此时的气温是零下九度。 除了极热和极冷,丹佛的天气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极干。从多雨之都飞来的我一到机场变发现口干舌燥,到了酒店发现连双眼都干燥无比。平时用量的面霜和饮料根本不够用,晚上我恨不得起来溺死在浴缸里。从丹佛回来我发现双手布满无比细小的伤口,都是干裂之后没有用足够的护手霜造成的。 与西雅图downtown的繁华不同,丹佛公司的所在是一个扔在美国任何地方都不会有区别的工业园区。一周的时间,从窗口望出去,都看不到任何绿色,简直是满目荒凉。回到西雅图,一出机场看到外面淅淅沥沥的小雨和满目的绿色,我简直像濒死的鱼跳进了水里。 然而丹佛也并不是一无四处。许多人留在丹佛,是因为它广袤的群山。从Hyatt十八楼的Bar看出去,整个落基山脉横亘在丹佛的西部,如群龙起伏,覆盖着白雪皑皑。飞机起飞的十分钟内,美景尽收眼底,代价是随后两个小时舷窗外一无所有、连公路都看不到的北美大陆。
冬中余雪在
文/王小心 那天和同事出去吃饭,一个刚从毛里求斯度假回来的哥们说,他在日本上空看到了富士山,很美丽。我说,远在天边,近在眼前。瑞尼尔山与富士山同一形状,海拔更高,都经过雪与火的洗礼。2012年九月,从西雅图回芝加哥的飞机上,机长突然广播:“大家伙儿可以从窗口往下看,我们现在正飞过瑞尼尔山的上空。”那是什么样的感觉呢?飘渺的云层下,仿佛黑白照片的瑞尼尔山口正对着我,在无法企及的、荒凉的大地上,矗立着白雪与灰烬覆盖的火山。在那一刻,我不是地球上的乘客,而是空降到月球上的旅客,仿佛世界尽头的荒凉与广袤在我眼前一览无余。 在所有的自然景观中,山脉是我最爱的一种。在青海支教的时候,在黄石旅行的时候,在欧洲翻越阿尔卑斯山的时候。它们不分白天黑夜地矗立在那里,白日看起来壮丽,夜晚看起来凛然。将暮未暮的时候,天空呈现极深的蓝色,而山脊上笼罩着一层近乎白色的光辉,仿佛是给狼人照亮的踪迹。它们在月光下闪烁着微微的光芒,有如遥远的古堡,而树林是它的禁卫军,一丛丛指向天空的树杈令人肃然而无法亲近。我是没有办法改变它的;我只能让它改变我。 瑞尼尔山(Mount Rainier)就是给我留下如此印象的山峰之一。曾经想过开车从芝加哥沿90号公路到来西雅图,本地同学吃惊地睁大了眼:“冬天开车走90号,你疯了?两座山:洛基山,喀斯喀特山!”北达科他、蒙大拿,确实是美国最荒凉的、电视剧中越狱犯才会藏身的地方,我放弃了这个念头。而瑞尼尔山,正是喀斯喀特山脉的主峰之一。 瑞尼尔山是个非常奇异的地方。如果在中国的西部,人迹罕至的高原上,一座座雪山巍然立于崇山峻岭之间,非常壮观,但也觉得这地方是该有这些东西。而在临近大海、海拔非常低的地方,一座雪山拔地而起,某天在临海的城市的观光,蓦然回首,发现巍峨的雪山仿佛与你近在咫尺,与城市里的地标建筑交相辉映;即使在盛夏八月,雪山上的皑皑白雪也历历在目,明暗交织,仿佛月球表面银色白色的暗影。这时,你不禁感叹,好一座白日月球啊! 这就是雪山与火山的独特景观。只有火山的喷发会让海拔瞬间隆起至可怕的高度,高海拔又让火山很快被白雪覆盖。瑞尼尔山与日本的富士山属于同一种类型,都是仍然在活跃期的活火山。即使小小的岩浆喷发,也能让泥石流淹没至几十英里之外的城镇,毁灭人类百十年来的辛苦劳作。在这壮美的自然景观前,没有人会不产生自身渺小的感情,从而产生对自然的崇拜之情。 瑞尼尔山是地球上记录降雪最多的地方,因充沛的太平洋水汽就在邻近,沿着山脉一路上升,形成高海拔地区巨大的雪量。1971至1972年的冬季,这里一冬天下了2850厘米的雪。充沛的雨水肥沃了华盛顿州的土地,所有华盛顿州的车牌上都印着瑞尼尔山的标志,自豪地写着:Evergreen State ——永绿州。在这片纬度与黑龙江省相近的土地上,瑞尼尔山无疑是这里的人们巨大的宝藏与生命的源泉。 是的,毋庸怀疑,这里也是滑雪者的圣地。虽然离开车三小时的温哥华Wistler还有差距,但西雅图的雪场、雪季均让一般地区望而兴叹。这里有7/24不间断下雪的Stevens Pass雪场,直落数百米的几乎垂直的雪道,还有山顶上可以看日出的小屋。一直到四月底,我们仍可以驱车上山,而上山的路程好似王维的雪溪图。最重要的,到山顶的前一秒还在飘雨,一到山顶,绝对是飞雪皑皑,连油门都不那么沉重了。 Stevens Pass: 从西雅图405或5号向北,转522再转2号公路大约一个半小时。雪季门票大约200-400美元,不限时。山顶有出租雪具(39美金/天),但在山下随处可见有瑞尼尔山标志的户外用品店租会更便宜。 http://wangxiaoxin.net
车轮上的我
去年九月的一个傍晚,我开着一辆现代Sante Fe在小镇上晃悠,忽然身后警灯一闪,警笛一叫,一名警察叔叔把我拦了下来。第一次被警察Pull over的我战战兢兢从书包里把id取出来,双手放在方向盘上不敢动,脸上肌肉紧张得直哆嗦还要装出一副笑脸问他how are you,就是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事。结果警察叔叔比我还要和蔼,说女士你知道么,你的后灯不亮了,刚才转弯很危险,要赶紧去修啊。 作为在美国从来没进过修车铺的我,此时如同无头苍蝇一样不知何去何从。我们班有一哥们,每天脸上笑嘻嘻地从不隐瞒自己的性向,是德国大众的最忠实粉丝。据说他从幼儿园起就确立了要进大众工作的愿望,而且这个愿望从未动摇过。来自美国西南沙漠的他是修车、买车、装车的一把好手,从幼儿园的乐高积木锻炼起,到自己买二手车拆装再卖出去挣钱,据说已经达到了车神的境界。跟车神哥哥一说,他二话没说,开着自己的VW领我到某个我至今未记住名字的车店买好灯泡,操起螺丝刀,三下五除二把我的灯罩卸下,灵活地把各种分不出颜色的电线接上,让我的车重放光明。我只能在旁边捧着某次在停车场撞裂的灯罩,听着他嘲笑我竟然能用块胶布把灯贴上,崇拜地看着他边修车边给我讲他在沙漠开车的各种传奇经历。车修完了,我们也成了朋友。 修车如同医生。医生看人,他们看车。同样是望闻问切,下周稳准狠,别人半天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他们轻轻巧巧四两拨千斤就能搞定。这样的技能,绝对是从童年时坐在父母车轮上就开始被熏陶被潜移默化,如同中国人学习炒菜或自行车一样,是生存本领,也是生活乐趣。有车有房的美国中产阶级,周末丈夫最爱做的事不是鼓捣花园就是鼓捣车库,那是他们的cave,可以钻进去享受偷得浮生半日闲的时光。 童年没有在美国生活过的我,这辈子对车不敢有任何技能上的奢望。然而在美国,车是必备用品,无车寸步难行。最早住在南加,那是典型是用“how long time driving”来衡量距离的地区,沿海的高速公路上,一辆辆SUV、minivan开得飞快,导致被北京的蜗牛交通惯坏的我直接被吓得不轻,直接挂掉了一次路考。 其实美国的路考很容易,起码比北京容易。美国人不知手动挡为何物,人人都开一辆“挂块骨头狗都会开”的自动挡。我的第一辆车是辆剧老爷的minivan,快二十年了,除了电池老挂掉之外竟然没有任何问题,我和bird两人开着这辆巨大无比的车去了LA,沙漠,边境,逛遍了南加的山山水水。 当然,在家里有一个男人的情况下,主要的开车者是他。虽然南加出门言必称高速,但我竟然不怎么敢上,这也是被宠坏的表现之一。我周围的家庭,大部分也是如此,我见过一个在南加住了五年开车只开local的女人,当然,她已经比大部分从来没有开过车的女人好很多了。 我的车技被锻炼出来,是在住到芝加哥后。一个人在中西部地区生活,车也换成了SUV,每天街趴,每周挪车,与交通灯与罚款单作斗争,其乐无穷。为了省钱,是绝对不会租公寓停车位的;于是就有了无数次深夜徘徊在街头四处找停车位的日子;夏天有扫街,冬天有snow ban,停在不同的街道上,每周都有固定的时间不能停车。每周不同的挪车时间是对记忆力的一大考验,即使记在手机上闹钟提醒,也还是被罚款过;但停车的辉煌战绩是每次停车下来,看到前后不足十厘米的空挡,觉得开车技术又大有长进。 人都是被逼出来的。一个人在中西部的生活让我从不敢上高速的菜鸟变成了可以开车载同学去另一个州的司机;也在开学时来回机场无数次迎接新生顺便赚点零花钱(考虑到我车的mileage,基本上零利润)。但比起美国同学成长的车轮上的天赋本领,我还是差了很多,也许永远都赶不上。去年夏天和同学去黄石和大提顿国家公园,横穿三个州,每天十小时以上的车程,崇山峻岭,海拔起落,从黄石南门到北门,东门到西门,全由一个大三的美国女孩完成。他们不论男女,就是有这种在大山大川间纵横捭阖的勇气,他们的身上流着殖民地拓荒者的血。最惊险的一次,是半夜在黑魆魆的森林里我们开车回家,副驾座上的男生突然大喊:“停车停车停车!”疾驶的车急刹车停下之后,只见一头通体颜色比黑夜还要黑的野牦牛与我们堪堪擦肩而过,再晚一秒钟,不知道谁会变成谁的夜宵。 现在到了西雅图,是第一次每日开车通勤。终于换了一辆新车,蓝色,叫Cornflower blue,矢车菊一般的蓝色。我唯一可以评论车的地方就是颜色,这点也被车神同学嘲笑过。本来可以坐公共汽车,很方便,也很环保。但是,坐在公共汽车里,总是有不能控制的焦虑感觉。每次红绿灯一停,我就恨不得跳下车走路回家。开车到park & ride,即使每天只节约了十分钟,也觉得自己控制了时间,更控制了交通工具。西雅图多雨,在早晨或者傍晚的雨雾蒙蒙中,开车仿佛在绿色的花园中穿行。上礼拜我开车经过一棵樱花树,就种在安全岛上。我的车像鱼一样从树下游弋而过,带起一阵风,樱花的花瓣两三片飘进车里,这种感觉,又岂是公共交通能比的呢。 所以我劝在美国的所有人学车开车。不管是博士后老婆、全职主妇、学生,开车都是四海一家的解决之道。班上有个小妹最近去了湾区工作,我每日在qq上不辞辛苦地劝她买车。在这里,车如同中国人的菜篮、自行车、公交月票,是不可或缺的生活。 车神同学后来去了福特。很好的公司,很大的公司,只是不是他最初的梦想。得知我买新车后此哥们在我的Facebook上留言: Where is Ford? 说好的Ford呢?他曾允诺给我员工折扣。下面有人回说,哥们,where is your VW?他回到:In my heart, always in my heart! 此同学现在著名炒房团热点地区底特律,住着月租一千上下三层的小楼。让我们祝愿他早日实现人生的终极梦想吧。
我们所在的世界
在西雅图,上班的路上要过两座桥,一个湖,一条高速公路。很奇怪地,在高速公路的路边有一站,孤零零的一个站伫立在疾驶而过的车水马龙中间。每次路过这个站,我都会想起村上春树在《1Q84》中描写的那个高速公路的出口,青豆穿着套装,顺着螺旋楼梯,一层一层地往下走。现存的世界就这样在她的脚步中流逝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新的世界,一个从不存在的历史中创造出来的世界。 《1Q84》真好看。既有现实,又有幻想,还有村上的狡黠。总觉得村上是个智商很高的人,带着居高临下的笔触看这个世界。他书中的人物都是无父无母(或事实上不存在)、单身一人,自己的内心世界与外部几乎是隔绝的。看青豆和天吾两个毫不相干的故事一点一点串接起来,两个人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这个不可能的世界中产生共鸣,并给读者提供智力游戏的机会。 与以前相比,我倒是觉得村上的写作风格不那么天马行空了,更多了流行小说甚至影视文学的感觉。青豆去刺杀领袖一段,几乎可以听到《教父》里艾尔·帕西诺从洗手间走出来的那一段呼啸而过的冲水声,紧张极了。可是天吾的故事也照样紧张,只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爱情与性欲的紧张。青豆与天吾分属《挪威的森林》中绿子与直子的部分,两者的生活和情感有风格上的不同,但又微妙地统一起来。 书还没有看完,不能最后下结论。但每天清晨坐在上班的班车上看一段,西雅图窗外雾蒙蒙的风景与书中的奇妙情节结合起来,是异常和谐的。这书让人惦记着,又不过分狗血让人想要在凌晨四点读完,是很好的消遣读物。每次从书中抬起头来,公车轰轰烈烈进入西雅图downtown交通的地下隧道,我总会想,书中的世界,与书外的世界到底区别何在呢?这是我们所在的世界。这窗外永远阴沉或变幻的天气,一成不变的上班族,如仪式般每日准时说“Good Morning”的司机,是否与1Q84,或者2Q13有某些共同点呢? 也许我永远不知道答案。
给爸爸的生日赞歌
我现在的年龄,比爸妈生我时的年龄还要大了。 我有时想,如果让现在的我和那时候的爸爸对话,我们会聊什么?如果我可以穿越时空到我小的时候,佐为同龄的我们,可以聊聊水利农田、生态系统,社会建设事业发展,或者谈谈三国历史;最有可能是聊聊音乐,比如拉个小提琴什么的。是的,所有的这些共同话题,都是我从小耳濡目染的。 爸爸做的事情大约是农田水利、防汛抗旱一类,所以我现在对这些工程有天然的爱好,比如桥梁、水库、自然生态系统。我喜欢高低起伏的丘陵,丘陵上高高挺拔的常绿阔叶针叶林,夏秋时节各种刚采摘的带着泥土的桔子,柚子,放在铺满松针的木头箱子里,一直能吃到冬天。 他给我讲三国。晚饭后散步的时候,会给我节选似的,讲里面最著名的小故事。草船借箭、赤壁大战,听到失街亭的时候我对诸葛亮充满了深深的同情,反复追问他三国里面哪国实力最强,结果还是没有听到满意的答案。 小的时候,我觉得爸爸每天都在无止无尽地开会之中。他是公务员,所以我对公务员的概念就是开会,作报告,写稿子,还有免费拿回家的铅笔和稿纸,300格一页的。还在上幼儿园的时候我会在爸爸开会的时候进去听,看叔叔们抽烟云雾缭绕,爸爸一本正经地说着大人的话,与在家里跟我说话完全不同。我可以在桌椅间戳戳点点,和小朋友打闹。现在回想起来,基本就和我女儿被抱到我先生的电脑前面的状态一样,学着爸爸的样子伸出手指猛戳键盘,得意洋洋,在爸爸的怀里无法无天,一副指点江山的模样。 那时候单位大院的大人们叫爸爸“小王”,叫我则是“小小王”。一转眼,小小王变成了小王,小王也变成老王了。 其实回过头来看,爸爸绝对是个文艺男青年。他大学的专业是测绘,而且是航空测绘,就是拿着透明纸和铅笔描画涂点的那种,这本来就是个极其文青的专业。小时候我用绘图纸粘风筝,家里有最古老的计算机,输入一段代码,可以打出来九九乘法表。我能在美国人面前引以为豪的数学,没准就是那些绘图纸和计算机给我打下的基础。他会做木工,小时候住过十几年的那个家,地上的漆还是他和妈妈涂的。他自己学拉二胡,小提琴,虽然不甚规范。他会上山采草药,懂得区分药草和其他植物。他会游泳,而且每种泳姿都会。我的象棋、游泳、羽毛球都是他教的。他的字典上用蓝黑钢笔写着他名字的英文读音:Heish-Ai。他还能上山打蛇,用剥下来的蛇皮做二胡的蒙面。这一点是当代文青们绝对比不了的。他的爱好很多,上手很快,但每一项都不是精通。后来我发现,我在这一点上简直就是他的翻版。我们都做过很多事情,涉及过很多领域,兴之所至,随手拈来,然后丢弃一旁,再也不管不顾。 所以,性格这个东西骨子里还是遗传父母的宿命,逃不了的。 所幸有这么多爱好,爸爸的退休生活是绝对单调不了的。这种兴之所至的精神现在发挥到了种菜、钓鱼、学英语上。聪明人的好处是学东西快,看看就会,不用费力。他种了空心菜、南瓜、白菜,还钓到了大头鱼。他每天都在博客里炫耀——嗯,我刚发现,连写作这个爱好我们也是一脉相承的。 爸爸今年六十岁了。我看着他从三十岁到六十岁,然而在我脑海里,他和妈妈的改变微乎其微,除了两鬓略添的白发。其实不止是脑海里,他真的是甚少改变,从身材到发型,到动作手势。去年我做了一张他抱着小时候的我和现在的我女儿的拼接图,所有人都惊呼你爸真的完全没变。 其实我知道迟早会变的。万物生长,天地循环,哪里有不变的道理?在人生的每个阶段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就已经很知足了。 我觉得他是知足的人。像每一个普通人一样,他在人生中也有过各种起落。风光有时,落寞也有时。但他能看淡这一切,并把这条道理教给我和我先生。进入社会以后,大家对我的评价常常是从容平淡。我知道这一点也是遗传爸爸,我们都不会过分关注某件事情,对大部分事情看得很开,尽量让自己想通或尝试了解别人的想法。所以他的人生虽然没有大富大贵,但有我和妈妈(当然主要是妈妈)平当从容地陪伴,也是种幸福了。 我祝六十岁的爸爸生日快乐。这么多年来,我就给他写过这么一篇文章,对于一个陪伴自己三十年的人来说,实在是太少了。但我本身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他的翻版,所以他也该偷着乐了吧。
纪念阿兰,一个弹吉他的朋友
写这篇日志的时候,豆瓣电台正在给我播放着一首不知名的吉他曲,旋律欢快而动听。我要在这里写的,也是一个弹吉他的朋友。他在几天前,主动选择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而远在大洋彼岸的我,听到这个消息是在好几天之后。我们的朋友圈没有交集,我也是偶然在微博上看到了别的朋友发出的消息,才知道他已故去的。 我们是朋友;不是很熟的那种,见过几面,在网上聊聊天。认识也是偶然——可能还是一塌糊涂BBS上吧,他发帖,说有一场演出,需要找把小提琴。那时候我才本科大四,小提琴还没有忘光,又因为保了研而整天无所事事,于是就义无反顾回了帖。见到他,觉得就是个小孩儿,提着把吉他,给我张琴谱,是《圣母颂》。我从来没有和吉他合奏过,问他,吉他还能和提琴合奏啊?他说可以。一练习,很合拍,很美。平缓的旋律渐渐流淌出来。小提琴是主旋律,但基本上是他托着我在走,是很有安全感的合作者。 我完全忘记那次演出了,但我从此认识了阿兰。 阿兰比我小一级,不同系,他有很多的爱好,我并不了解。我知道他在高中时因为抑郁休学过一年,但从他的外表上完全看不出来。如果他不是最外向的,起码也绝不内向。我一度以为,我搞错了他的病。他自己也并不隐瞒,所以我完全没把这些放在心上。对一个交往不多的朋友,也确实不太会去关心这些事。 他一般跟我谈音乐,谈他的理想,阿兰这个名字的由来,他如何学习吉他,如何准备做一个职业吉他手。我惊异于他短短几年中的进步,同时暗自为我小时候被逼学了那么多年琴还没学出个名堂感到羞愧。我是个现实的人,觉得人总要靠专业找工作,在音乐上是几乎不可能实现职业的理想的。但同时,我又为他锲而不舍的精神所感动,觉得他也许具备成功的特质。但这些想法,我始终没有说出来过。 后来我们又合作了一两次。那时我已经读研究生了,记得是在南配殿的一次演出。多年不拉小提琴终于忘得差不多了,结束之后回宿舍,发现BBS上我们的节目广受恶评。我心有不甘跟他吐槽,他还反过来安慰我说,都是玩嘛,高兴就好,不用管别人怎么说。 后来回忆起我在校园中的岁月,总有一个镜头是我们在30楼前的紫藤架下面排练(那会儿找不到别的地方),有低年级同学经过,还赞叹两声,或者上来跟我们交流一下乐器常识什么的。 那年月,我们都觉得音乐是必要的东西。 毕业之后我工作了几年,然后又出国了,从此再也没有见过阿兰。出国之前一个春天下着大雨的夜晚,我和一个朋友去朝阳文化馆听周云蓬。在中场休息的时候,一个抱着吉他的男孩盘腿坐在舞台的地上,为观众弹着一些过场的旋律。我心里一动:那不是阿兰吗?他仿佛和周云蓬他们很熟,是来帮朋友热场子的。我没有上去招呼他,但欣慰地想,原来他还在坚持他的理想啊。 如果我知道那是最后一次见他,我一定会上去跟他打个招呼,说,我很高兴看到你还在弹吉他,弹越来越好的吉他。 出国之后我在msn上跟他聊过几次,他开始做一些日化产品,护手霜、香水等等,还跟我说,这些东西的成本都很低,可以在化学实验室里做出来,关键是市场营销,现在在找人试用,大概是这个意思的话。我跟他推荐了另一个在4A工作的朋友,阿兰还真去找到了她,那个朋友之后还去听过阿兰的演出。 我知道阿兰还在谈吉他,还在做香水护肤品,我觉得他终于找到了一条能用上自己专业的路,同时也能兼顾自己的爱好。我很高兴,但也并没有特别去关注他。 直到前天我在微博上看到他去世的消息。 人在年轻时认识的朋友,也许有一小部分可以保持联系,但大部分是越走越远的;并非因为不想,而是因为不能。有了自己的家庭、住所、工作、孩子,柴米油盐,雨雪风霜,没有校园这样一个封闭盒子一样的东西把我们装起来,在社会这块交叉纵横的大平地上,大家偶然地相遇,打个招呼,然后继续各自走各自的路。 而那些你觉得总有机会再见面的朋友,就这样再也没有见过面了。 我希望阿兰去了他想去的地方,也希望活着的朋友,那些在年轻的时候认识的朋友活得好;因为这个世界这么大,不知道能否见面,但若能知道你在世界的某个角落活得幸福,跟我一样整天柴米油盐、工作家庭,为琐事烦恼,就是对我们年轻时代友谊的最好怀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