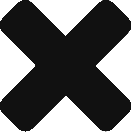在人生的头十六年里,我和大部分中国三线城市长大的姑娘一样,连外国人都很少见过。英语是有口音的老师教的,语法和词汇好于听力和会话;最远去过的地方是上海,妈妈念叨了桂林许久但是从来没去过。
在祖国的八十年代,这是大部分家庭的状况。十六岁的时候,我突然考上了北大。从京九线坐二十六个小时的火车来到金秋的北京,我好像来到了世界的另一面。
北京占有了我大部分的青春。我和天南海北的同学坐火车和大巴逛遍了中国的山山水水,从南京到东北,从苏杭园林到黄土高原。那时候对旅行的概念还仅限于“去一个地方”,看看景点,看看古迹,谈一场心满意足的恋爱,然后回到原地。
大学毕业的时候,我做出了一个让大部分瞠目结舌的选择。我决定去青藏高原上的一个国家级贫困县,一个回族和土族自治县的的藏族“民族中学”支教一年。在我学习的专业毕业的学院,大部分同学毕业去的是法院、检察院、公安局,或者律所,后来他们中的大部分都成为中国崛起的黄金十年中的中坚力量。
而我,选择了远离。
我从来就是一个疏离的人。客气的朋友用“闲云野鹤”来恭维我,美国人直接说我“Indifferent”。我在看书看电影时哭点巨低,但在现实生活中正好相反。高原是疏离的最好选择。那所海拔3000米的民族中学在青藏高原上,背后是雄伟的祁连山脉。高原的阳光经过雪山的反射,明亮刺眼,把我晒脱了皮,一片一片的红色。我教的学生都有高原红,校领导、县领导请我们吃饭,每顿必喝,喝完必唱,清脆的藏语山歌在黑夜中远远地回荡开来。我第一次发现,世界原来这么大,大到我看不见边际。那是家乡南方的竹林和北京的城墙所不能围住的;我如同飞出太阳系的探测器,前面有无穷无尽的范围等待我去探索。
教书之余,我常去学校外面的一家名为广惠寺的喇嘛寺。有时候门关着,我就坐在门槛上,看红色屋檐下面蓝蓝的天空。里面的喇嘛请我进去喝茶,我看着他们转动转经筒,一圈一圈,上面金色的花纹已经被磨平。初冬的下午,高原上的天气冷得渗人,而屋子里烧着煤炉,弥漫着酥油茶和香火的味道。铜碗上沁出热气凝结的水珠,密密麻麻,像永远也看不完的、我不认识的佛经。那个喇嘛和我聊天,说起他的家乡,他学佛的安排,他还俗后的计划。我给他拍了照片,但总是没有机会给他。后来我离开了学校,回到北京读研,有一天我突然意识到,我可能再也见不到他了。这个陪我度过一个安宁下午的人,那些陪我度过许多无聊时光的学生娃娃,那些沉默的群山,它们成为我生活中某个时间、某个空间的一部分,我们互相成为对方的回忆,然后在脑海中的某个区段,定格了。
我不再刻意做“去某个地方”的旅行,然而这一年的生活在别处对我的影响是,我选择了一次又一次地疏离当下的生活。这些年来,我一直在用眼睛看,用耳朵听。地球上有太多地方可以去了:我去了欧洲,在丹麦人的家里一住就是半年,管女主人叫妈妈,管她的女儿叫妹妹。我走遍了欧洲,后来又去了加州,去了芝加哥,去了北美大陆的许多地方。不论到什么地方,我都尽量把自己当成一个“在其中”的居民而非“观察者”。美国警察鸣笛让我靠边停车的时候,我像在北京一样,陪着笑脸,双手递出驾照,战战兢兢地说“大哥您好”;在加州永不改变的晴天下,我仰头呼吸着紫外线,心里想起的是青海高远的天空,寂静的空气。生活永远都是相似的:在这里生活,与在那里生活,除了每月缴费的煤气公司的名字不一样,并没有什么不同。
不同的是人。我认识了许许多多的人,他们有着不同的面容,不同的故事,不同的性格,不同的想法。在走过了太多地方、认识了太多人之后,国籍、肤色、种族的概念在我头脑中逐渐模糊起来:我认识了在俄国长大、在瑞士受教育的美国人;我认识了在美国工作的波兰人;我认识了在德国工作的日本人,说的德语和日语我全都不懂,只能从他的德语中找出我认识的丹麦语词汇;我认识住在丹麦一辈子,然而头发眼睛都是黑色的库尔德人。我开始学会不以他们所说的语言来辨别一个人,或者说我根本不辨别人,因为每个人都是不同的:我只看他们的衣着,他们的眼睛,听他们的故事。这就是世界主义的含义。一个人比他所走过的地方的总和还多——不是旅行成就了你,而是你成就了自己的人生。
由于练就了这样的一身本领,我开始喜欢和人打交道。由于在许多地方都生活过,与陌生人见面,我总能找到可以与之交流的话题。我开始和哥本哈根城里来的设计师谈我住过的丹麦乡下,和美国中西部的学生谈他们家乡的玉米地,和公司的同事谈他们上大学时打工卖景点门票的经历。从加州辗转到芝加哥到西雅图,我永远在“定居”与“迁徙”中徘徊,我开始不刻意去旅游,因为我发现,只要在生活中每天都能发现新的事物,那旅游其实是不以地点的转移而定义的。
在西雅图这座雨城,我白天在一座家大业大、被我称为“美国国企”的时尚零售公司工作,安安静静地做我的市场分析,淡定自若地处理来自全国各地的大数据,妄图从中分析出时尚的趋势、顾客的走向、东海岸的暴风雨对销售数据的影响;我见到形形色色的人,开形形色色的会,听到各大区的经理讲述他们顾客的故事,和他们自己的故事;晚上,我的心中汹涌着文字,试图把那些来自平淡生活的东西升华成超越凡世的凝固体,并把它写下来:我的生活、我的生命,和我生命中遇到的值得写下来的人和事情。
我不担心我的文字有一天会枯竭,在我的生命枯竭之前。其实每个人的生命,都可以写成无数的值得纪念的东西。然而世界主义者的悲哀是,我失去了故乡。每个他乡都似故乡,每个故乡都不是魂牵梦萦的那一个。那个二十年前的南方,十几年前的高原,十年前的北京,若干年前的丹麦小镇,都在频繁的拆迁与重建之中遗失了;即使没有空间意义上的拆建,那些人——曾经在某个阶段与你有着某种交集的人——也一去不复返了,如同陈凯歌拍《百花深处》时的疯子,站在胡同口的残垣断壁,徒然地想象着曾经的生活。我生活在每一个他乡,可惜我不能同时生活在每一个他乡。
这,就是一个世界主义者的自白。